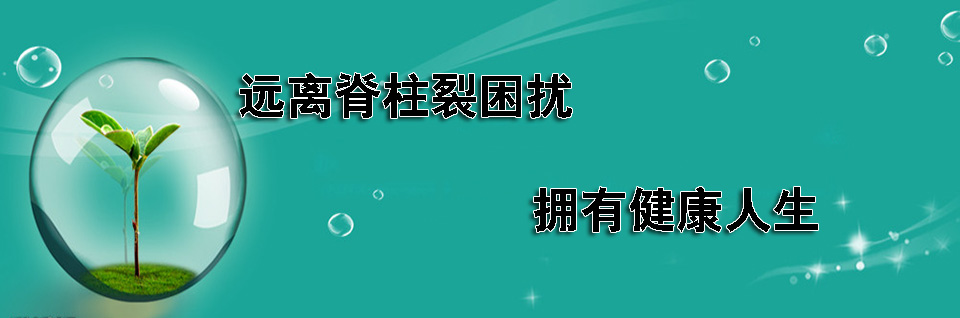当前位置:脊柱裂 > 脊柱裂护理 > 咸鱼的中二流水账middot疯狂 >
咸鱼的中二流水账middot疯狂
北京治疗白癜风医院那家比较好 http://www.bdfyy999.com/index.html夏末,零星反复的疫情总算告一段落。随着最后一名已知感染者在邻省净化的消息分发至各处,我终于从繁杂的防疫文书事务中解脱出来,得以遵从医嘱,到海边虚掷半月光阴。交接完案头的文件,轻装简行赶上了途径渔村的马车。甩开西去的日头,穿过层层叠叠的丘陵,两个季度以来的伏案工作强迫我在摇晃沉闷的车厢里依旧保持着混沌的清醒。等到晕乎乎地下了车,已是黄昏。站在路边,眼前的这重山障背后,依稀可见有炊烟升起。渔村就在海湾边上的一处山岙。巴掌大的平地背靠着起起伏伏的、密布着甘蔗林的山丘,另一侧是颇为陡峭的山崖,穿插崎岖着一条还算平整的山路,通向山下的浅滩,路边稀疏竖着几根竹竿。我预备暂住的居所就在山路的尽头。背对夕阳,在向下的山路慢慢走着,胸中残存的浊郁叫满带柴火味道的空气尽数取代——据医生所言,这对我双肺与神经的健康至关重要。望一望余晖下的海滩,陆续归港的渔船,我警戒了数月的神经逐渐放下了防备。山路尽头的小屋是我叔祖的产业。一间简单的木板房,不过好在五脏俱全。叔祖一家曾以捕鱼为业,虽则叔祖本家不在此处,但叔祖母的娘家就在山岙渔村。此间的海湾是极好的良港,叔祖与叔祖母就将此处作为出海途中暂避风浪的中转,故此搭了这间板房。我年幼时也来过这里,还在叔祖母的娘家寄住过不短的时间。当时岛上垦殖庄园爆发了如今年一般、使人疯狂的疫病,只有远在边缘的这么几个渔村未被波及。而今疫病再起又再平,二位老人家已过世多年,子女不再在海上求活,不过这间小屋依旧得以保留——饱经海风侵蚀却依旧稳固。在听说我需要盐分充足的海风疗养后,堂兄就把这锈迹斑斑的钥匙交到了我手上,算起来已经阔别此处整整三十六年了。接下来的时间过得极平静。我依旧保持着在城里的作息,每日刚清晨就醒来,还赶得上随日出而来的潮水。渔民们起得更早,往往我推开遮板探出头的时候,只来得及见到几根高高低低的桅杆溶化在缓缓升起的粼粼朝阳之中。而后就趁着日头未满,去渔村后的山上闲逛一番,或在村居中与未出海的老人小孩一起坐着剥剥各种果子。临近中午,要么是到村头买些饮食,要么就在同剥果子的村民家里蹭一顿饭。再然后就回到小屋里闷头大睡,直至午后潮退时分,和一帮赤脚的小孩去赶海。直到傍晚潮水再次涨起来的时候,回到屋里蒸些杂粮饭,烧些赶海收获的小海鲜,拎一瓶总督送的葡萄酒,搬一张折叠桌,就支在屋外头,坐在海风里。等到黄昏,被余晖映得明黄如一体的海天之交,高高低低的桅杆一点一点升起来,大大小小的渔船从一个个小点变得逐渐清晰可辨。晒得黝黑的渔夫拖着一天的渔获上岸,他们的妻子,坚毅的渔家女们则留在船上把渔网晾好。在我看来是天量的活计,就这样有条不紊的、以不可思议的熟练与速度被完成。渔船归港大致一刻钟后,年幼寄住时认识的伙伴阿丹——现在也是如我一般的中年人了,只是看起来较我更为沧桑——和他的妻子就能完成各自的分工,和我一同坐在屋前小桌上就着海螺酒饭,聊聊今日在海上的见闻。他们的孩子和一只来历不明的狸猫则看似不经意的在桌边走来走去,屡败屡战地筹划如何偷点酒吃。至于曾经一起玩耍的其他人,已在风浪中漂泊了十年未归,一同出海的人中,只有阿丹侥幸抱住了一块船板,在某个黑夜被潮水送回了海滩。此处没有疍户,晚饭后海滩上就没有人了。潮水涌到山崖边,泊在海湾一侧的渔船随着海浪起起伏伏,船上点着的船灯明明灭灭。同样的两点灯光也在滩头与村口的竹竿上闪烁着,分别标记着潮水与人类王国的分界,稀疏疏的亮点呼应着从海上顺着山路通向渔村。船灯接力的最后一站在各家屋头,由渔家女们在入睡前挑着挂在门头。这是本地的习俗,方便风浪中迷失归途的亡灵能透过弥漫的海雾望到各家归港的航灯。到此处的次日,我也向当年的伙伴讨了一盏船灯,在屋边立了竹竿。这段时间里,每晚睡前我都会把灯挂上,寄希望藉此能在离开见到那几位童年玩伴。已经是第十一天了,船灯挂了十天依然无人造访。今晚海雾算不上浓厚,夏末的风凉爽清新,我拖了一张躺椅放在崖边。初来的时候是月盈,十一天过去,残月的光亮只能算是聊胜于无。船灯的光在透镜的聚焦下穿透力强但范围不广,数十里外的亮点依旧清晰可见,而二十步开外的躺椅周边就照不见东西。好在天空还有亮光,那是满天星斗在深蓝的天穹深处燃烧放出的光,透过厚薄不均的雾气泻在山边海上。星光下,黑绸一般的海面泛着淡银色的圆点,延伸自无法捉摸的世界尽头,呼应着一路向上的,指引亡魂的船灯。绳帆与渔网这些原本糅合在背景之中无法分辨的配件,此时在海风中流动起来,如较黑绸更为漆黑的杂乱线条舞动在银色的光点之间。璀璨华美的星光持续吸引着我,我就这么靠在躺椅上呆看了不知多久。长夜渐深,或许是我的错觉,天空与星辰似乎在朝相反的方向加速而行。深蓝的天空愈发幽暗,燃烧的星辰愈发明亮,好像要将宇宙十亿百亿年积攒的能量尽数耗尽一般。在岛上多年,我从未没见过这样的星空。头顶的南十字星座是众多星辰中最为明亮的,星芒明亮得几乎要融为一体,像一柄耀目的钥匙,十字的短边笃定坚毅地指向本应黯淡、此时却异常明亮的南极座包围拱卫之中的,幽深如万年不见天日的地下洞穴一般的南天极。我的神思早被空中异象所摄,不知何时已从躺椅站起来,目光焦点被莫名的力量死死钉在南十字星座正中,手脚僵直动弹不得。或许是看了太久,我的视野中除去仍在燃烧的南十字星座与南极座以外,余下的漫天星辰正逐渐转为昏暗,围绕着燃烧着的两极旋转。终于,旋转着的南天银河几乎全部熄灭,南十字的银光达到了巅峰。就在银芒大盛的那一瞬间,位于南十字内的漆黑的煤袋星云突兀裂出一道本不存在的连续光隙,斩断了这岛民眼中翱翔天空之鹤的昂扬鹤首。当象征执法官的鹤首被贯穿的刹那,南极座所在的天区隐约传来一声叹息,原本灼目反常的、拱卫着南天极的南极座三角溃败般迅速变暗。我的耳边忽然响起不可描述的低语,如蚊蚋之声般微不可查,又如重槌般砸穿我的耳膜,震得我目眩神迷。这眼前一花的空当,我仿佛看到南十字构成的银色钥匙撕裂夜空,爆发的星光望南天极笔直而去,一颗炽烈的流星在星光刺破南天极的瞬间,从幽黑的谜穴坠落,拖着耀眼的光痕迅速坠向海面。我下意识向前迈了几步,想看明白那流星是否落在海面。可漫天的星辰异象骤然而止,海面的雾气猛地增厚,阻拦住我的视线。就像是深陷幻术的人,难以抑制的冲动紧紧握住了我的心脏,每一次搏动都伴随着响起于脑海的低语,驱使我一探究竟。我不顾一切地突破愈发浓厚的海雾,冲下山路,冲到象征着夏季潮水界限的巨石边。正当我就要不顾一切冲向泛着漆黑线条的、黑绸般流动的海水时,我的脚下被什么有些柔软滑腻的东西一绊,一跤跌在缓缓后退向未知天际的潮水中。苦涩的咸水味道刺激着我的鼻腔口腔,连续呛了几口水后我的神思清明了许多,我也无法确信适才的低语是否真实存在——至少现在只能听到呼啸的海风。手脚并用地从浅水中爬起,惊魂未定的我狼狈地站在海雾中,大脑一片空白,眼前一片灰雾。在海雾中,我失去了方向。船灯!还有船灯!苦咸的味道稍稍退去,理智重新夺回了被茫然惶惑窃据的大脑。我四下张望,终于在左后方见到了不负所望的、坚定地闪烁着的黄色灯光。灯光没有上下起伏,这是潮水界石上放的那盏船灯。我突然想起方才似乎被什么柔软滑腻的东西绊倒。在这灰白的迷雾中,看着如悬浮着的黄色光点,一种莫名的恐怖涌上心头。可潮水席卷后的海滩难以预测,除却船灯标记的道路外,选择其他方向无异于听天由命,而适才的诡异冲动低语确信无疑地告诉我,切不可听天由命。无奈之下,我只能硬着头皮朝着界石的方向摸索而去。或许星空幻术的威力已经退去了,这几步路走得毫无障碍。我扶着界石,潮水已经退后了不少,周围是湿润的沙地,抬头看看山路半腰一闪一闪的黄光——那是我的小屋。路途并不远,但周围实在太黑了,我的目光落在手边的船灯上,为什么不用这盏灯照亮呢?我的心里有个声音轻轻说道。有惊无险的,我提着灯回到了小屋前,看着海雾中影影绰绰的熟悉的木板房,我的灵魂终于安定下来。谨慎地抬头看向星空,南十字、南极座安然在原地,漫天星辰与平日一般无二。或许是浓雾带来的幻觉?我在心中这样安慰自己,对另一种可能讳莫如深。总算逃过一劫,长舒一口气,我决定回屋休息。就在推开房门的时候,我的余光扫到立在崖边的船灯闪烁了一下,变得黯淡将熄。大概是海雾从灯罩的缝隙侵入了。想到方才全赖这黄色光点的指引才成功返回,我走到屋里取出手提箱里的老式手枪揣在怀中,预备用手上的灯把老灯替换下来。换灯的工作非常顺利。老灯灯罩的铁箍松开了,过于潮湿的海风稀释了作为燃料的煤油。明天找村里的兼职铁匠重新紧一紧应当还能用,我如是想到。本来也就无事了,可刚才幻境一般的经历始终啃啮着我的心脏。提着老灯,看着闪烁的微弱灯光,我壮起胆子朝天空偷眼望了一眼。夜空平静,毫无波澜,就像今晚之前的十个夜晚一样。赶紧回去吧,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可就在我准备反身回屋时,耳边响起了一阵不同于风声的窸窣响动。“完了。”我险些喊出声,又慌忙咬紧嘴唇,左手把紧了船灯,右手探进怀里放在了手枪上。周遭什么也没有,那响动似乎来自于山崖边,就在躺椅边上。我舔了舔嘴唇,谨慎地朝前走了几步。还是什么都没有。躺椅边上是一丛灌木杂草,或许是在枝杈之间?我把船灯放在躺椅上,空出一只手拨开树枝,还望山崖下看了一眼。还是什么都没有。大概是我的错觉吧,我想到,心里放松了不少,那就回屋休息吧,可能是刚才惊着了。我转过身,伸手去够放在椅子上的灯。就在此时,一阵反常湿冷的海风如蟒蛇信子,又如章鱼触手般在我背上一掠而过。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刚勾到船灯的手指下意识一抓。被勾住悬耳的船灯晃了晃,就在我急剧放大的瞳孔中倒在了椅面上,顺着光滑向下微微弯曲的椅面,“咣”一声闷响掉在地上,“咔嚓”,灯罩裂开,雾气涌入,本就昏暗的灯光负隅闪了闪,就此熄灭。几乎在灯光熄灭的瞬间,恐惧疯狂上涌,阻塞在我的喉头。雾很厚,我能看到二十几步外的船灯,却一点也看不见周遭的物事。黑暗中背上冰冷阴寒的感觉顺着脊柱一点一点往上,冷不防在我的颈椎关节上轻轻舔了一口。“啊!”我无法自禁地发出一声惊悚的尖叫,不顾一切地转过身,抓着手枪的右手快速抽出,朝面前“砰砰”连开数枪,然后回身拔腿就跑。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看到悬在半空的船灯,甚至方才直视手枪击发的火光后,连船灯都不那么亮了,耳膜也被枪声震得轰轰作响。但这也够了,小屋也不过就是二三十步的距离,三四秒就到了!“先生……”可就在我的腿将拔未拔,人将撤未撤时,右前方突然传来虚弱的男性人声,低沉虚弱,满载痛苦,但异常清晰,仿佛就是耳边低语。是人?说实话,我本不是什么胆小的人。但适才无法自制、险些跳海的异常实在吓坏了我,更兼孤身一人独陷黑暗,一点风吹草动带来的恐惧都会被无限放大,听到附近有人声,这声音又带着虚弱,我的心反而安定了几分。“先生……”大概是没有听到我的回复,那声音又试探地响起,似乎变得更痛苦了。“是谁在那?”说来也快,心安定几分后神思也变得冷静清明了许多,我摸了摸手枪弹筒,还有一颗子弹。“我……我,是……我。”那声音停顿了片刻,又重新响起,“我,我在这里。“这位先生,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水里……海上很黑……只有这里有光,我不知还有哪里可去。”难道是遭遇海难的渔民或船员?我心里想着,握紧手枪,慢慢地朝声音来源挪过去,“您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就在……刚刚,先生。我醒来的时候就在海滩上,从这里的斜坡爬上来的,这里有光,先生。”我闻言一愣,想起刚刚在海滩上绊的那一跤,难道是……声音的来源似乎就在附近,我不自觉松开了手枪,半蹲着在地上摸索,果然摸到了湿漉漉的、柔软冰凉的一团。“噢,先生。”地上那人又发出了痛苦的声音。“您怎么了,受伤了吗?”“我不知道……我在海里漂了太久。”“唔……”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打了个岔子随口问道,“您……这里是A城下的X村,先生,您是从哪来的?我能帮到您吗?”“先生。”男人听到村名的时候显得有些激动,“您是说,这里是X村?”“是的。”“原来是这样,是这里的光……噢,先生,我或许听起来像个疯子,但是,先生,请您告诉我这是哪一年?”“XXXX年,夏末。”“……”男人沉默了。“您……还好吗?”我问道,心想着这难道是传说中失事海员,流落孤岛求生数年终于重返文明世界的励志故事。“十年了……我……我竟然在那里过了十年。”男人突然啜泣起来,似乎印证了我的猜测。男人的啜泣持续着,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保持着不太舒服的蹲姿,直到男人的声音突然变得惊恐,我似乎能察觉到他的脸此时应当是极度扭曲的:“噢,不!不!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回到这里!”这近乎是嚎叫了。充满自责与疯狂的嚎叫声后,对话暂时停止了,我与这位不知何处来的神秘男子诡异的沉默中静止了一会儿。“先生,我猜您并不在此长住。”来历不明的来访者突然开口道。“我不是,我只是来这里暂住半月。”“太好了,太好了。”男人听起来放下了心中重担。我还没及张口追问,一只冰冷湿滑又出奇柔软的不知什么东西突然碰到了我的膝盖,又一触即回,我心里一惊,下意识摸了摸寒入骨髓的半月板,却意外摸到了一柄形似匕首的东西,很轻,可就是这个几乎没有重量的东西让我觉得彻骨深寒。“杀了我吧,先生,杀了我。”男人突然恳求道。“什么?先生,您……”“您是不是觉得我疯了。不,先生,我没有。只是我在那里呆了太久,我不能回去。您知道吗,我是X村人,可我在那地方呆了太久,我不能回去。”男人精神错乱般快速说道。“您是本村人?太棒了,希瓦女士是我的叔祖母,您认识她吗?”没想到竟然是本村的渔民,这位在外漂泊了十年的可怜人大概是在海上被吓坏了,“我现在搀您到屋里休息,您住在哪里,天亮了我就送您回去。”“希瓦……女士……噢,您是……”声音停顿了片刻,又变得激动起来,“不,你们不能看到我。先生,快,快杀了我!就用这把匕首,杀了我!取出我的心脏,趁着退潮扔到潮水里。让海水带走我身上的罪恶。但先生,我恳求您,不要把我的尸体抛到海里,就从这个山崖推下去,我记得这里有个山崖,下面是乱礁潮洞,这样我就能够留在这里,但没有人会见到我……至少在我腐烂分解之前。先生,不要告诉任何人。”“您在说什么?您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不会杀死您的。休息一晚,明天我送您回去。”我有些不耐烦于迷障一般的黑暗,预备起身去把挂在小屋边的船灯取过来。“以希瓦女士的名义,不要灯光,您不可以看到我。”神秘人仿佛能看见我回头看灯的动作,我感到我的脚被之前那种冰冷的触感锁住了,“杀了我,先生,快杀了我,把我推下去,然后回到您的屋子里,明天一早就回城。不要告诉任何人。”“您……”“先生,我无法向您解释。地狱,我是从地狱回来的。去过地狱的人不该回到人间。”“您在说什么?”“地狱,那是深埋海底的地狱!礁石山谷里的魔鬼古堡!千面雕像注视下的禁忌之地。天哪,我竟然在那里过了十年。”疯狂的声音停顿了片刻,“先生,杀了我,然后回城去!杀了我,趁我还能把握这瞬间的清明。尼尔,我亲爱的尼尔,看在希瓦女士的份上,看在我的份上,快杀了我!”“您……认识我?”我惊讶于这神秘的男人竟然叫得出我的名字。“是的,我是萨哈,您年幼时的玩伴!那不是瘟疫,那是疯狂!”“萨哈!我以为你死了,和他们一起……”“他们都死了,全都死了!只有我,萨哈,在地狱里被困了十年,十年的疯狂,也作了十年的伥鬼。”萨哈痛苦地嚎叫道,“我能感觉到,它就在附近,我已经能听到它的低语了。快,尼尔,趁现在,趁现在我是清醒的,快杀了我。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能在这里再次陷入疯狂。尼尔,让我解脱吧,让我免于刻在脑髓里的低语,免于抽离灵魂的凝视,免于旁观自己沦为屠夫的折磨。”“萨哈,你在说什么?什么低语,什么凝视?”我想要跟上童年玩伴的话语,但萨哈的语速太快,声音忽大忽小,实在听得我头昏脑涨,不明所以。“他疯了。”突然我背后传来冷冷的声音,还有些熟悉。“阿丹!”在地上蜷着的萨哈惊叫出声,“你怎么在这!”
莫非他真有黑暗中视物的能力?没想到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个。
“是的,我亲爱的萨哈。”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背后的阿丹说道,我没有转头去看,但我觉得他就站在屋边,甚至还觉得他舔了舔嘴唇,“或许,他们并非都死了。”这两人的对话让我觉得没头没脑。“不,我分明记得……”萨哈的惊恐愈甚。“你记错了,我亲爱的朋友。”阿丹打断了他,依旧用不带温度的声音说道,“欢迎回家。”“你……你回来多久了?”“足够久了,亲爱的,足够久了。”“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噢,不!是他放你回来的!你竟然屈服了!你竟然做了他的信徒!还回到了这里!天哪,尼尔!不要回头,跳下去,离开这里,不要回……”萨哈说道一半,突然尖叫起来。“……唔……”我想问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我说不出话来,此前锤击大脑的感觉愈发明显。“是的,我的朋友,是那位大人放我回来的。我很好奇,萨哈,你是怎么背叛大人的意志的?或者说,你是怎么窃据这具血肉祭坛的。”萨哈没有回应,继续他非人的嚎叫,充满痛苦。“看来大人就要降临了。”阿丹冰冷的声音罕见的出现了一丝波动,轻叹一声,“那就让亲爱的尼尔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吧。”话音方落的瞬间,我只觉大脑几乎要炸裂开来,杂乱无章的低语涌进我的脑海,又觉得有一根冰冷的、滑腻的——就像刚才在海滩上、在蜷缩在地上的萨哈身上触碰到的,冰冷的、滑腻柔软的东西,爬上了我的后脑,“转过来,亲爱的。”阿丹说道,在杂乱的低语中竟然分外清晰,无法拒绝。渔村方向的灯光不知什么时候全部熄灭了,小屋边悬挂的船灯也变得十分虚弱,原本橙黄的火焰有转为灰蓝色的倾向。一个人影立在屋边,正好在灯光的范围之外,浓雾中看不见面目,但身上的衣物分明属于阿丹。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入我的视界的。我根本不曾转过身去,我的灵魂似乎被抽离了躯体,在不可反驳的命令下不知以何种方式转了过去。我甚至能看到黑暗中自己僵立的身体,但我看不到是什么在触碰我的后脑,看不到我的身体与立在屋边的阿丹之间有什么连接,也看不到地上挣扎嚎叫的萨哈。“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叛徒先生的秘密是什么。”这是阿丹的声音。
大脑陡然刺痛,一千只无法描述的眼睛在我的神海中一闪而过。“原来是这样,没想到传说竟然是真的。既然这是灵魂归港的信灯,那么……”我看到我握枪的右手缓缓举起来,枪口指向逐渐虚弱的船灯。“砰!”黑暗瞬间淹没了我的视界,萨哈持续的尖叫突然消失,连我脑海中混乱的低语也停止了。就这样?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觉得周遭黑暗安静得恐怖。可就在这“恐怖”的念头萌生的瞬间,不可名状的低语再次响起,就像是三千名落水的海员在风雨交加中苦苦哀求,又像是三千个疯子在熊熊火焰中凄厉嚎叫。分明已经陷入黑暗的我竟然看见我那无可言说的恐惧具象成了一只巨大粗壮的触手,从脚底开始,一寸一寸地,徐图缓进地,缠住了我的双腿,缠住了我的双臂与躯干,缠住了脖颈,缠住了我的下颌,伸进了我的嘴里。我感到一股冰冷滑腻沿着食道向下,却意外探入了胸腔,裹住了我的心脏。“这大概就是透心凉吧。”……初秋,据A城官员报告,本已平息的瘟疫在其下辖某渔村重新爆发。目前,各省已加强瘟疫戒备,净化工作将持续进行。郑咸鱼但讲陈文,不说新语。
最新文章
热点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
推荐文章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