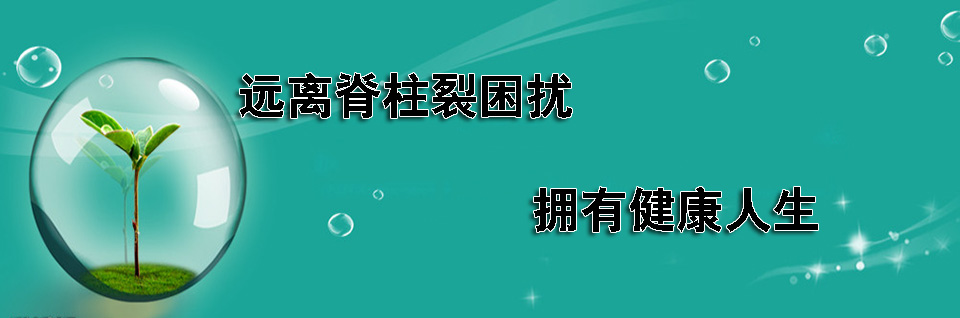当前位置:脊柱裂 > 脊柱裂护理 > 球场爱情故事戏剧时刻 >
球场爱情故事戏剧时刻
幸福对于有的人来说,总是迟到早退,命运反复玩弄给予之后再掠夺的游戏。不管是谁,每次射门前都无法预言是不是能进吧。拿到球、面对门的时候,保留起脚的勇气,就是不亚于进球的胜利。
今天为大家推荐「戏剧时刻」短篇小说写作比赛「渴望之物」组入围作品,作者静岛的小说《射门》——
射门
静岛
(一)
15年前,22岁的我和23岁的倪凯在操场练点球的时候,看到了舞蹈系的女生走过。
窈窕,步履有弹性,颈部、肩膀、胸部的线条迷人,白皙得像一生都只晒过月亮。
倪凯看得有点呆,我看着他,也有点呆。
「我差点也成为这样的人,你相信吗?」
倪凯转头看我,眼里都是笑,他走过来用守门员手套揉我的短发:「郑胜男,你真会开玩笑。那得是差了多大的点啊。」
他总是这样,把我认真说的话当做玩笑,而我,也渐渐学会了用说笑话的方式说出真心话。
「倪凯,你还真挺帅的,我是说踢球的时候。」
「倪凯,风流债少欠一点行不行,英语系那个妹子都来找我诉苦了。」
「倪凯,当代文学的笔记可以借你,晚上陪我喝酒。为什么?我想你陪我喝酒不行吗?」
我知道倪凯懂得那些玩笑话背后的认真,他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子,有着极好的女人缘,惯于在若干美女之间平行穿梭,他怎么会不懂得。
他不戳穿我,正如我不戳穿他,都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明不白地做朋友。
我试图理解他的苦心,这苦心背后的动机,恐怕不外乎他想要占有一个有名的刺头女生的爱意,这自然不是皇冠上的宝石,但驾驭了一匹野马,应该一样能满足年轻男人的虚荣心。
进大学军训,倪凯帮我怼了嘴巴不干净的教官,在烈日下被罚站1小时军姿,明明可以装中暑晕倒的,他偏偏站够了时间才瘫倒在地,隔天又第一时间背着全班最胖的女生去校卫生院,转身还去小卖部买了卫生巾叫我送过去。
倪凯是那么一视同仁的温柔、细心、坦荡,而又坚强,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他,大学四年,我用所有心思接近他、分析他,我敢说我是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
按说越是了解,越是容易失望,人都是经不起分析的,但我一边看不起他,一边深爱着他,爱得太重,轻易克服了理性分析后的不屑,他想要什么,我都愿意给他,连他不想要的,我都想塞到他手里。
我看了很多书,也写了一点文章,我明白的,人生中总有这样一次劫数,你只怕对方不索取,不自私,不留恋。
我认了就是。
几个月后,我带着学校女足队拿到了全市女足邀请赛冠军。和队友拍完照,我筋疲力尽躺在球场上,倪凯拿着运动水壶的吸管递到我嘴里,我不喘气地喝着,他狠命把吸管从我牙里拔出来:「喝太快心脏会受不了,小心挂了。」
「心脏病死应该很爽快,一下子就挂了,挺好。」
「放屁,死就是死,死就是痛苦的,没有什么死是爽快的。」
倪凯在我身边躺下来,我们贴得太近了,他一定会闻到我身上的臭汗味,应该挪开一点的,然而我真的舍不得动。
我抬头看天上的云彩,云彩很好,如果真的有天堂,云彩上的魂灵们一定很拥挤吧。
「我爸就是心脏病死的。他35岁的时候,我2年级,陪着他和老同学踢球,他忽然就倒下了,很快,我们都没反应过来,应该很爽快吧。」
我知道倪凯在转头看我,他的目光打在我左脸上,很热。我们那么近,如果我也转头看他……
我能听到自己的心砰砰砰地跳动着,像是射门前的一秒。
所有踢过球的人都知道,踢球最刺激的就是拿着球面对球门、所有人看着你的瞬间,那一刻永远无法真正有足够的把握,如果考虑风速、角度、力度,就几乎势必会失败。
只能什么都不管,起脚射门。这件事说起来太简单,像那样做起来太难,很少有人有这样的勇气。
倪凯特训了我大半年,我是个好前锋,我每次都敢射门。
我只是不敢转头。
我们靠得太近了,转头的话,我会忍不住亲他的吧,而我刚刚说出一个惹他同情的秘密,以倪凯那么温柔的性格,一定不会推开我。
但不能是因为同情,绝对不能。
那次我如果转头,我们后来的命运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真想知道啊。
我们无声地继续躺着,风驱赶着云彩,急匆匆地不知道要去哪里,而时间因为他停滞了,我哪里也不想去。
倪凯忽然抓住我的手腕,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发现自己被他抓得站了起来。
「走,请你喝酒。」
我跟着他走了几步,发现有点不对劲,髋关节隐约疼,右腿不听话了。
「大概刚才跑得太狠,肌肉拉伤了。」
倪凯搀着我走到车棚,我靠他半抱着才坐到后座上。去饭店的路上我小心抓着他的球衣,我低头看着我们的影子,它们分开、汇拢、重叠,再分开……
我们要了8瓶啤酒,一人一半,喝得很开心。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那么开心地喝酒。
(二)
第二天,我的髋关节更痛了,右腿已经几乎无法用力,上下台阶的时候必须扶着扶手,用左脚单脚跳。
医院,医院检查,医生们在我的脊椎末端看到一个可疑的空腔,内里似乎有组织或者液体,医生的初步判断是肿瘤,只是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还有一些争议。
「所以要做个手术?」我拿着检查单子问爷爷奶奶,他们没绷住,开始哭了。
他们身旁,还有一对父母,也刚刚拿到检查结果,看到我爷爷奶奶哭了,也跟着呜呜地哭了出来。
他们的儿子坐在边上,看着有点面熟,戴着我校的校徽,一看就是个雏儿,他和我一样一脸懵逼。
我示意男孩和我去小卖部买水,他非常听话地站了起来,一米八左右的个头,走路也和我一样是瘸的,我们两个就这么一瘸一拐、一高一矮地逃离了案发现场。
去小卖部的路上,我和男孩交换了名字,他叫庄子墨,刚大一,音乐系的。
庄子墨兴奋地说:「我想起来了,我看过你踢球,你可以啊,过人很漂亮,起脚特别干脆。」
人在忽然得到坏消息的时候,是会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滞后性的,那时候我和庄子墨完全没有意识到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什么,所以我们是镇定的。
水钱是他掏的,「怎么能让女孩子请客呢?」。他冲着我笑,眼睛是丹凤眼,笑起来眯成两条细缝,仍然亮得惊人,假以时日,应该是很有女人缘的。
活检结果要一周后出来,我们联手劝说长辈答应我们继续上学:我要准备论文,而庄子墨要参加学校乐队的排练,医生也说了目前正常学习生活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真的需要手术,接下来请假的日子还长得很。
庄子墨是乐队的贝斯手,我起哄,叫他不要去排练了:「反正没人在乎贝斯手,你还是歇着吧。」
「放屁,JasonNewsted牛逼不牛逼吧?」
医院大门的时候,我和庄子墨热烈地探讨起Metallica哪首歌最好。大人们看着我们,已经止住了泪,想哭而不敢哭的模样,他们互相交换了手机号。
到大学校门口的时候,我们一起坚定拒绝了家长送我们回宿舍的要求。
我们一瘸一拐走到了食堂打饭,叫了最贵的小炒,都没有吃下几口。
倪凯在食堂就注意到了我们,他后来说,他当时就想过来和我聊天:「怕耽误你难得的桃花运,就没敢。」
我没有看到他。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我总是能从人群里一眼就找出他来,但那天开始,这项特异功能消失了。
十五年过去了,闭上眼睛,我还可以看到当时我看到的,天空中确凿地飘来了一团乌云,挡住了所有其他重要的、不重要的,我只能用放肆的笑来证明自己的勇敢,似乎勇敢就可以让我远离噩运。
我知道庄子墨也是一样的,全世界只有他和我看到了同一团乌云。吃饭的时候,他讲笑话的声音比我还响。
幸好有他啊,那团乌云同时笼罩了我和他,仅仅是他也存在这件事情,就对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吃完饭,庄子墨送我回寝室,我在宿舍楼下和他挥手告别,我们两个说了太久的笑话,我的脸都酸了。
我同样没有看到倪凯跟着我们,看到了也一样,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三)
第二天上午,我照常去上课。
倪凯问我腿怎么样了,我笑笑:「不知道,等下周活检报告。」
「不想笑的时候就别笑。」他抢过我的包背着:「下午选修课,翘了吧,陪你喝酒去。」
「医生说不能喝酒。下午我要去查资料写论文。你论文还没开题吧?」
「要你管。」
「管不了。把包给我,我要去食堂。」
我和倪凯拉扯了一下,书和笔记本掉了出来,还有我昨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写的单子。
很多年后我看了电影《遗愿清单》,原来人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反应都是一致的:一项项写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世界上真正会认真为未来做计划的人,都是知道自己可能没有未来的人。
倪凯蹲下,把东西捡起来塞回我包里:「这么严重?开始写遗嘱了?」
「你滚蛋。」
我抢过包,往食堂挪了几步,倪凯走过来不由分说背起了我:「你别乱蹬,乱蹬我更累,别人都在看了。」
我趴在他背上,不敢再动。我知道他是个温柔的人,不知道他有这么温柔,他越温柔我越难过,这个世界本来没多少我会舍不得的东西,死了也就是死了,他让我越来越舍不得死了,简直可恶。
吃饭的时候倪凯主动问起了我爸爸,做了四年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好兄弟,这是他第一次用雾气蒙蒙的眼睛看着我。
谁也没有办法抵挡这样的眼睛吧,我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我爸重男轻女得厉害,我妈生下我之后,他就没给过我妈好脸色。我8岁那年,爸妈准备离婚,我爸猝死,我妈失踪了,十几年来没有联系过我。
说的时候挺痛快的,带着一种自暴自弃的冷静,我的人生就是这么稀烂的,原本我花了很大力气才藏好那些千疮百孔,终于发现毫无必要了。
倪凯的眼睛里,雾气越来越重,等我终于说完,他拉着我的手,不再是上次那样拉着手腕,而是手指扣住我的手指,「郑胜男,你这个傻子,你不会有事的,我不许你有事。做我女朋友吧。」
上一次和人说起我家的事情,是在高二,和最要好的女同学。起因是她对我倾诉了自己失败的单恋,她爱上了自己爸爸的同事,一个已婚的男人。她说完这些开始痛哭,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而我深知人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动物,当交出一个秘密的时候,总是指望对方给出相当程度的秘密来作为质押,所以我咬咬牙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了她。
当时她搂着我说:「原来你比我可怜多了,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但之后,她渐渐远离了我。我曾经不明白,后来懂了,同情他人的不幸,是一件善良的事情,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要和他人共同分担这种不幸,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正的不幸不是一个事件,它是一种状态,或者说疾病,它并不会真正痊愈,本能告诉我们,接近不幸者,势必也被传染不幸。
倪凯只是被自己瞬间的感动和一贯的温柔坑了。四年了,这四年他明明知道我对他的情意远不止朋友那么简单,而他一直漂亮地躲闪着,如今,他想做我的救命稻草了。
用爱温暖、拯救一个快死的人,这肯定比和舞蹈系系花恋爱更有成就感吧。
我看着他,感受他手掌的力量和温度,我多希望这一切发生在几天前的那个下午,我们一起看云彩的下午,我还没有说出我爸去世理由前的下午,打动他的只是我,而不是我的不幸,和他试图让自己成为救世主的自我崇高。
我摇摇头。
「为什么?你和那个瘸子什么关系?」
「我现在也是瘸子。」
「你不会永远瘸的。」
「这倒是,死了就不瘸了。」
聊不下去了。
倪凯坚持送我到宿舍楼下,问我:「你和你妈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
我知道他看到了,我的遗愿清单上第一条就写着:见妈妈一面。
「她叫什么名字?我帮你找,我爸是警察。」
(四)
出活检结果前一天的晚上,倪凯往我宿舍打了好几次电话,我都叫室友撒谎说我不在。
最后一个电话是庄子墨打来的:「下楼走走?」
我毫不犹豫地下楼和他会合。
庄子墨带着我去了操场。我们一瘸一拐走在空旷而平坦的跑道上。庄子墨问我听不听朴树,当然听了,他从背包里拿出CD机和耳机,我们一人一个耳朵听起来,是朴树的《我去年》专辑。
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肩并肩沉默地走着,毛姆写过,「两人肩并肩地走路本身就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按说那个夜晚,无论如何也不该和愉快有任何关系,但走着走着,褶皱着、紧缩着的什么被打开了。
我看到了头上的流云、月亮、星星,髋关节的疼痛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晚风柔软,而我并不孤独。
放到《我去年》的时候,庄子墨说:「我想跑一下。」
我说:「我也想。」
他牵着我的手跑了起来,两个瘸子的奔跑,为了照顾耳机朝彼此的方向歪着头奔跑。已经身处年的我们,因为一首年的歌发疯奔跑。
「没有人仰望蓝天/繁星密布的夜/我和我那些秘密又能唱给谁听……」
只跑了小半圈,我的髋关节已经无法支撑,庄子墨也是,我们一起停了下来。他仍然抓着我的手:「现在想想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是啊,总觉得跨千年,应该会发生什么,现在想起来,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
在黑暗中,我知道他和我一样,被同样的恐惧和渴望控制了。
不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就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如果可以这样,一辈子都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该多好。
我们绕着操场走,手始终牵在一起,像两个相依为命的人,不是像,本来就是。
我们聊到了人生的意义。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和人聊起过这个话题,估计庄子墨也是。
那天晚上他说了什么,我已经无法清晰地记得。十几年来,我经常回忆那个夜晚,回忆他的声音,他的体温,他言语中的停顿,他才18岁,我22岁,关于人生,我们能说出什么值得记住的话呢?
我们只是聊着,一直聊着。星光月色下的跑道往前铺展着,看不到终点。
「为什么剪这么短的头发,你养长发一定很好看。」庄子墨问。
「因为我爸爸喜欢男孩子,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养,不许养长头发,不许穿裙子。」
「你都那么大了,还听他的啊?」
「我8岁的时候,他死了。那天我陪他去踢球,路上他问我,如果他和我妈离婚了,我跟谁。我想也没想,就说跟妈妈,这是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庄子墨停了下来。
「我爸留下了很多东西,球衣、球鞋、号码牌、护膝、袜子、球票、帽子……我陪爷爷奶奶把这些都烧了。只有推子没烧,后来我就拿那个推子给自己推头发,坏了之后又买了个新推子……」
庄子墨拥抱我,俯身在我耳边说:「不是你的错。」
我在他怀里发抖:「我真的想都没想就回答他了,哪怕我犹豫一下呢?」
他抱着我,很紧很紧地抱着。抬头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的我,月光真好。
我们接吻了。
「等我们都好了,你教我踢球。」
「等我们都好了,你教我弹贝斯。」
一直到我不再颤抖,庄子墨才松开了我。
转身的时候我看到了倪凯,我朝他笑笑。
爱上他太容易了,哪怕受尽期待、屈辱、患得患失的折磨,我都曾经坚信这份爱永远不会改变。
不爱他太难了,爱了四年,他让我感受了四年的孤独,而这个夜晚,我好像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被陪伴。
永远没有办法对倪凯解释清楚吧。
(五)
活检的结果出来了,我的运气特别好,我的确病了,但只是隐性脊柱裂造成的可逆的问题,那个让所有人担惊受怕的空腔里,只有一些害处不大的积液。
我开心地给庄子墨打电话,问他的情况,他妈妈哭着说:「如果我们的结果好,早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我要庄子墨家的地址,他妈妈说他不愿意给我,我让他接电话。
「我想来看你。」
「不用了,别同情我。」
「不是同情,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没时间喜欢你了。」
倪凯说到做到,帮我找到了我妈,这么多年,她原来一直和我生活在一个城市,我们的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
因为已经死不了,我不想见她,她拉着倪凯找到了我家,我怕爷爷奶奶受刺激,只能偷偷出去和她见面。
十几年不见,她老了一点,还是很漂亮,看到她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想象中那么恨她。我忽然想起来了,小时候我有多同情我妈。
从我记事开始,我爸礼拜六上午总是和大学同学去踢球。他曾经是大学朦胧诗社的社长,又是校足球队队长,文武全才,追到了我妈这个校花。
可惜不管是写诗还是踢球,都无法让我爸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以诗人的性格得罪了几任领导,以中国男足错失射门机会的运气错过了若干次下海赚钱的机会,三十多岁还只是个牢骚满腹的普通科员,他的脑袋上刻着「失败者」三个字。
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做中学英语教师的我妈找到一个兼职,每周六上午去给老外上英语课。我跟着我爸去球场,和我爸踢球的同学们每个都生了儿子,他们休息的时候会围着我和我爸开玩笑:「胜男长得不错的,留个长头发,以后给我做儿媳妇。」
玩笑是玩笑,背后未必有恶意,但对于我爸来说,想必是一种无法反抗的羞辱。
回想起来,当年的大学生是值钱的,那时候我爸的同学都已经在自己的单位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只有他不行。
他的成功只在足球场上。奔跑,过人,单刀,进球。干脆利落,毫不犹豫。
我记得他无数次这样的动作,他是球场上的英雄。
大人们的球赛结束,我爸会陪着我练球,颠球,传球、停球、过人,他教得很认真,哪次我假动作晃过了他,射门进球,他会大笑,和我击掌,那是我们难得的瞬间。
有次球赛,有人临时有事来不了,我爸拉着我下场:「胜男可以的。」
我爸的同学们看到他严肃的脸,没人反对。
我爸是左前锋,后卫都盯着他,我右前锋的位置根本没人防守,我爸疯狂跑动,赢得了一个小角度射门的空间,他抬眼看到我,传给了我。
不管过去多少年,我都能记得那次停球之后的瞬间,如果射丢了这个球,我爸会气死的吧,如果射进了,我爸一定很高兴。
怎么办?犹豫了一会儿,我把球传了出去,传丢了。
回家的路上,我爸闷头踩着自行车,我搂着他的腰正要道歉,他说了一句:「连射门都不敢,到底不是儿子,没有用。」
我从自行车后座上跳了下来,崴了脚,我爸并不理我,扬长而去。
我走回家的时候脚踝已经肿得透亮,我妈和我爸大吵。他喝醉了,给了我妈一耳光。
我爸就是这样的人。女人离开这样的男人,算不上坏人吧?
(六)
我妈哭了很久,我从她断断续续的话里拼凑出了很多当年的事情。
我爸死之前写了一封给我妈学校的信,大致内容是揭发她和老外学员的桃色事件,希望学校对她从重从严查处。这信还没来得及寄出去,被我爷爷奶奶藏好了,我妈和他们抢我,他们就拿出信来赶走了她。
「你搬家、转学,我不敢找你。我真的不是怕被人说,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可以怕的,我是怕别人知道了你不好过。反正知道不知道,你都要恨我,就不让你知道算了。」
原来,我不是被她当累赘轻易抛弃的。
但那又怎么样了?做错了就是做错了,告诉我真相,让我恨她,然后陪伴我,让我原谅她,难道不该是这样的吗?
我一言不发坐着,倪凯大概是看出了我在冷笑,他打岔:「阿姨,胜男说她以前差点也跳芭蕾舞,是吹牛吧?」
「不是,她小时候可是正经跳过小天鹅的。」
我妈从皮夹拿出一张照片,我穿着白色紧身衣,蓬蓬裙,芭蕾舞鞋,脸上画了两坨腮红,眉间还点了个红点。
「可爱吧?我走的时候她爷爷奶奶不准我带走东西,这张照片还是我偷偷拿走的。你后来还跳舞吗?」
小学一年级,我一个飞腿教训笑话我发型的男同学,舞蹈队的柳老师看到了,拉着我去舞蹈教室看基本功,我天生柔韧性很好,能够非常轻松的下腰、劈叉,肌肉发达,关节柔软,柳老师觉得挖到了好苗子:「郑胜男,跟我学芭蕾好不好?」
我看着舞蹈教室里的学姐,盘得一丝不苟的发髻,紧身衣,蓬蓬裙,红舞鞋,每个人都美得亮闪闪的,赶紧点头。
我入门得很快,跳舞也好,踢球也好,需要的除了柔韧、力量、平衡之外,还有吃苦的能耐。世界上不需要吃苦就能做好的事情本来也少。
每周六下午跳舞的事情,我不敢告诉我爸,告诉了我妈,我妈很支持,偷摸给我交了补课费,买了鞋子、裙子,骗我爸带我去学数学。我爸不疑有他,数学学得好,似乎也是一件非常男性化的事情,他很支持。
为了第一次公开演出,柳老师要我养长发,哪怕只能扎个小揪揪:「扎起头发,露出脸部线条和耳朵,才有舞者的样子。」
头发长起来可真慢啊,我每天都把头发往后撸,试着距离扎起小揪揪还有多少厘米。我妈偷偷给我头发上喷水,说是自己的学生Paul送的,「美国的生发水,应该能让你的头发长得快点儿。」
演出那天,Paul叫了出租车带我和我妈去少年宫,在后台,我给他们表演了我的舞蹈,第一手位,第二手位,雀跃,大跳,Paul看完鼓掌,用生硬的普通话说:「和你妈妈一样漂亮。」
那会儿我太高兴了,我爸是从来不会表扬我的,尤其不会说我漂亮,他对我最接近表扬的评价是「像个男孩」,所以那天,我扑上去拥抱了Paul。
我妈问我:「Paul叔叔好不好?」
我真心实意说:「好,特别好。」
曾经说出这样的话的我,让我说出这样的话的我妈,能被原谅吗?不可以吧。
我看着我妈:「你走了之后,我再也没跳舞过。」
我妈捂着自己的脸痛哭:「我真不敢想,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就是过来了。
没爹没娘的孩子能遇到的事情,我都遇到了,坏事情一件件发生,我咽下它们,咽不下就会被噎死。
除了倪凯、除了庄子墨,这十几年唯一发生的好事情,大概是我爱上了阅读和写作,它们帮助我构筑了一个虚幻而重要的场,让我看到很多比我更为痛苦的灵魂,安慰我:在生命和时光面前,一切都没有那么重要。
我给我妈递了张纸巾,这些年她一定也咽下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恨的了。
一切都没有那么重要。
(七)
十五年后,37岁的我,为了写一个校园背景的网剧,托倪凯回母校去呆半个月。
倪凯在校门口接我,他伸出右手,不知是想要摸我的头,还是想要接过我的行李,十几年没见,我们双方同时尴尬而客套地笑着,大概就是这个笑,让他的手臂在空中犹豫不决地划了个复杂的曲线,最后缩回去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郑胜男,十几年不见,你怎么没什么变化,还是活蹦乱跳的嘛。」
「哪里,都开始长白头发了。」
「我都快秃了。总算留长头发了啊,早该留了,漂亮多了。还踢球吗?」
「大学毕业之后就没踢过了。」
「可惜了。不过不踢球也好,白了很多。结婚了吗?」
「嘻嘻。」
倪凯看了我一眼,我也朝他看一眼。
我推着箱子跟着倪凯走,他一路絮絮叨叨说着,给我搞到了单人间,有空调有电视有宽带,除了没有独立洗手间之外,完全就是个不错的单身公寓;中文系的老师都打过招呼,我想去听课就随时去听;图书馆、食堂的卡他都给我办好了;他如今是系主任,做什么都方便……
话很密,像一块块飞速掉下来的俄罗斯方块,我慌乱地垒到一起,拼凑出结论:他这些年过得不错。
「倪主任,牛逼了啊。」
「还是郑编剧牛逼,你写的戏我都看了,有的还真行啊。」
拐过教学楼是翻修过的操场,红色的塑胶跑道,绿色的草坪,比十几年前漂亮多了。
球场上有几个男生在踢半场,倒脚来倒脚去。
我和倪凯看了一会儿,我摇摇头,他也笑了:「要不要下去教训他们一下?」
我给他看看我的高跟鞋:「还是你上吧。」
「我也不行了,看看这肚子。」
当年他踢球到一半总喜欢掀起球衣炫耀自己的六块腹肌,让迷恋他的女生发出此起彼伏的「啊」、「好帅」的感叹,没想到他也有这天。
我没忍住,捶了他肚子一下,我们都笑了,这次是真正的笑,十几年刻意回避彼此的时间在笑声里碎裂,笑完我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十五年不见了,你都好吗?」
我就知道这句话会来的,我摇摇头:「其实是十四年没见。」
「原来那次你也看到我了,为什么不叫住我呢?」
「你也看到我了,为什么不叫住我呢?」
确诊之后,虽然没有生命危险,治疗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休学了一年,每天都要医院理疗。
开始几天,我妈坚持陪我,她坐在我身边,抓着我的手,试图和我聊天。我总是塞上耳机。阳光斜斜打在我脸上,车窗缝里吹过来早春的风,她的声音偶尔会穿过歌曲与歌曲之间的空隙。
平心而论,我不是恨她,不是要惩罚她,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迟来的母爱。
我妈和倪凯商量之后,决定不再勉强我,医院。
后来好几个月,倪凯一直坐在我身边,像我妈一样拉着我的手,好像要把我牢牢拉在人间。
我曾经最想要拉着的手,如今拉着我了,然而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这前半辈子,遇到的所有好事情总是迟到早退,还是不要在乎,不要眷恋的好。
我从摇摇晃晃的车里,透过玻璃窗看着车窗外的人群。
那时候最常感受的是一种荒谬,我差一点就可能远离这热气腾腾的人间,而乘客们、路人们根本对我的幸运、对他们自己的幸运一无所知。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习惯了发呆和沉默,习惯在十字路口看着人流,想象他人的生活,想象面无表情的他们,内心曾有过、或正有着什么无法和人说的隐痛、遗憾和恐惧,想象他们如何掩盖或克服这一切,继续自己的生活。
很多次,我想对倪凯说这些,我想我可以和他分享很多,关于生活的残酷,生命的荒谬,而我掌握了让自己平静的秘诀:对重要的东西轻慢。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怕他不懂,更怕他懂。
我拄着拐杖拍了毕业照。
要离开的时候,倪凯给了我庄子墨的家庭
最新文章
热点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
推荐文章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