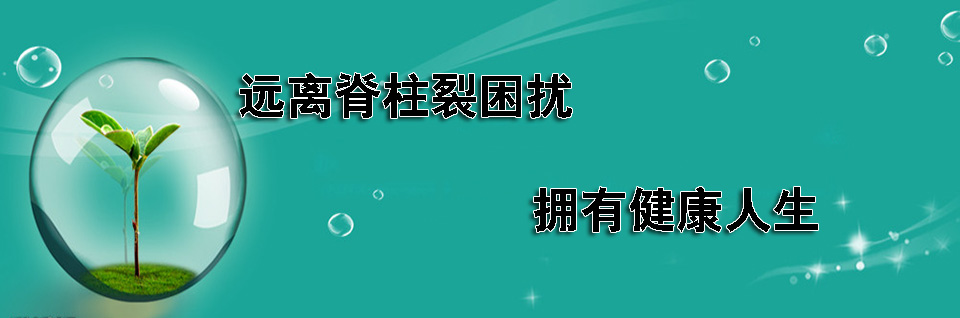当前位置:脊柱裂 > 脊柱裂症状 > 恐怖日记他记录了把妻子变成根雕的过程 >
恐怖日记他记录了把妻子变成根雕的过程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有个童年阴影,一直没和人说过:有天我发现,我爸会在半夜偷偷看我的日记。
我受不了被人窥探的感觉。狱警唐有耳告诉我,我这样的人千万别犯事儿,因为高墙里狱警为了管理犯人,可以随意翻阅他们的日记。
他就从日记里看到过很多秘密。
比如,三个同性恋犯人争风吃醋,其中一个人在日记里抱怨,“昨天我帮你把肥肉都挑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吃我给你打的饭,去吃那人的?”
还有一伙人准备打群架,为了保密,他们发明了一套密码,写在日记里传递消息。最后因为有人害怕了,主动向狱警汇报才败露。
但最令唐有耳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一本藏在枕头内的日记——里面详细描绘了虐杀一个女人的全过程。
我任职的这座监狱离县城二十多公里,以前叫做劳改队的时候,经常有犯人逃跑,有的至今没有抓回来。
但最近三年,监狱没发生大事,很多人都习惯了这种现状。
直到那天早上,在劳动区工作的犯人组长慌慌张张汇报,一个叫刘远征的犯人不见了,估计又是逃走了。
我们没有太吃惊。但是在检查刘远征日记的时候,上面虾爬蟹行的大字吓了我们一跳——“等我出去就把你杀掉。”
他非常详细地描写,怎么把一个女人绑起来,用烟头烫她的乳房,用小刀划开她的皮肤,让她的血一滴一滴往外淌,直到流干。
那个女人是他的老婆。
一打开刘远征的日记,几个老狱警都忍不住咦了一声:“这娃有点凶哦!”
犯人的日记是会被定期检查的,但刘远征除了给我们检查的本子外,还藏了一本在枕芯里。要不是因为他越狱后我们清点物品,根本不可能被发现。
那本破破烂烂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手绘的监狱附近地形图。画得很抽象,但主要建筑的位置基本真实。
更令人惊讶的是,每个警戒点有几个人值班,什么时候换岗,都有非常准确的标注。
刘远征的越狱计划,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周密。
他是个二进宫,上回因盗窃被判七年,这回还是同样的罪名,十二年。但这一次赶上了监狱改制,他被分到下井任务重的大队。
那是年,监狱还没有脱开劳改队的影子,井下工作非常危险,一钻进去,四五天不能出来,鼻子里全是厚厚的煤灰,炸矿的声音听一次,能让人耳鸣好几天。
几乎是一进来,刘远征就后悔了,开始在日记上谋划越狱。
当时的监狱除了监舍有围墙电网,大片的生活区、办公区可以有外人居住,普通居民的人数能占到犯人的三分之一。犯人和不少老乡都在煤矿干活,虽然有些限制,但彼此往来没办法绝对禁止。
借着外出干活的机会,他跟老乡把周围的地形、路线打听了个遍,又偷听狱警聊天估算排班规律,记下了我们抓逃工作大概的流程。
他甚至计划好了要在谁当班的时候逃跑——有个狱警曾不小心碰落一个凳子误伤了他,刘远征要让自己脱逃的责任落在他头上。
按照这样的计划,在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跑出了警戒线。
对于追捕工作,不少人都有点生疏,几乎每个人都以自己所知加上一些想象在议论此事。
狱警们略显忙乱后,开了一个短会,如何守卡,如何搜山,分组进行。
刘远征越狱之前,正在井口煤仓干活。大约5点40分,他离开队伍,他的组长6点20分才发现,等最外圈的警戒线收到消息开始拦截,已经快7点钟。
别的犯人可能会浪费这个时间差,但凭刘远征对地形的熟悉程度,他肯定是直奔公路,一口气跑到四五公里外的小镇去了。
按照这个推测,我们把大批警力放在了外围。
刘远征决定越狱是在井口煤仓通宵夜班之后。
早饭的时候,他悄悄多拿了两个馒头揣在怀里。同组的罪犯都只顾着自己吃东西,完全没有注意他做了什么。
吃饱之后,神仙也要犯困。刘远征感觉自己眼皮也快张不开了,在心里掐着表算,不能睡、不能睡,熬过了他们,就能跑出去。
十多分钟过去,他觉得差不多了,佯装随意地站起身问:“我要去撒尿,有没有一起去的?”
几个昏昏欲睡的人不耐烦地挥手赶他走。刘远征从煤仓溜下去,直奔警戒线,远远看见值班室里的工人睡得东倒西歪。
有两件衣服是早就在外面藏好的。刘远征拿上衣服,用这辈子最快的奔跑速度跑过警戒线。
然后,他脱下外面破烂肮脏的班衣,在路旁的水沟里洗了一下脸,换上干净的衣服。他走到他上次服刑的地方,穿过几条熟悉的巷子,去敲舅舅的门。
刘远征的舅舅年轻时坐过牢,刑满后也住在监区附近。刘远征上次服刑时,经常趁能外出活动的时候,到舅舅家去坐一下。
但这次敲了半天并没有反应。刘远征背上一凉:他妈的,这可不是好兆头。
这时,隔壁的大娘被敲门声吵醒了,开门看到是刘远征,不知道他已经是二进宫,便说,你舅舅到成都去了。
应付了几句刘远征赶紧离开。
到哪里藏起来呢?他想到行人桥下那个废弃的矿井,又是一路狂奔,慌不择路溜了进去。
他找了个干燥的地方,勉强坐下。没有任何光源的废弃井洞非常黑,黑得让你感觉自己已经被吞噬,成为它的一部分。
时间非常难熬,刘远征背靠着坚硬冰凉的石头,好像自己也快变成石头一样僵硬。他壮着胆向更深处摸索,废弃井洞因为没有通风系统,越往井洞深处走,温度会比洞口更暖和一些。
但同时,深处还有蓄积的瓦斯,那是非常致命的毒气,如果浓度够高,只要吸入一口就能令人窒息。
刘远征走三步退两步,凭呼吸的困难程度估摸着周围瓦斯的浓度,好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稍微暖和又不闷得难受的地方。
通宵熬夜和两次狂奔让疲倦无法抗拒地压来,刚刚成功实施完的逃跑计划第一步也让他倍感轻松,最多三分钟,他就睡着了。
刘远征醒来的时候,饿意来袭,把两个馒头都吃了。矿井里有流水,非常苦,还有很重的硫磺味和霉味,但他还是喝了下去。
吃饱喝足,他慢慢摸到井口看了看:外面已经是晚上,路上有行人,好多人家的电视也还开着。
他非常谨慎地溜到一个可以看到舅舅家窗子的地方。没有灯,没人。他有点沮丧地回到洞里,又昏昏睡去。
饥饿是最难关闭的闹钟,再一次被饥饿唤醒的刘远征向井口摸去,突然发现天气更冷了,还有一股湿气渗进来。
下雨了,而且下得不小,从井口往外望去,就连略远一点的房屋和山林,都完全淹没在一片雨雾中。
井洞里暖和,那些警察肯定正在各个出入口淋着雨蹲他,甚至组织一群人搜山,冒着大雨在山林里摸爬滚打。
“累死你们,哼哼,你们哪晓得老子就在你们眼皮下面睡觉呢?”
他很得意,自己故意留下枕芯里那本日记,想引着警察以为自己跑远了,就会把有限的警力往外放,最后甚至关卡都会撤掉,这样他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坐着班车出去,杀掉那个女人。
想到那个女人,刘远征靠着井洞慢慢坐下来,脑海里浮现出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画面。
那是8年前,刘远征26岁。他从县城里回来帮家里挖地,一个姑娘洗完衣服从河边回来,从他身边走过,一股皂角的清香让他抬起头。
那一瞬间,他好像傻了一样,手里的锄头落下来,把刚买的解放鞋挖开了一个口子。他认得,那是村里的素芬,他第一次注意到素芬这么好看。
素芬笑他:“辉娃子,你咋子哟?小心把脚挖到起。”
刘远征怔怔地说不出话来,一直看着她走远。回家后他立刻找媒婆,让媒婆告诉素芬,只要她嫁给我,我就带她去城里打工。
那是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外面的世界对每一个农村长大的年轻人都有无比魅力,能从农村走出去就算是有本事了。
这个许诺一下戳中了素芬的心,她很快嫁给了刘远征。婚礼后没多久,小两口就扯着一提行李,坐上最便宜的火三轮,一头扎进了大城市。
那时候,他们都以为自己已经把井洞一样死气沉沉的日子抛在脑后,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刘远征的老家离监狱四五个小时车程。狱警找到素芬时,她正提着篮子要上街去卖鸡蛋,看到穿警服的人向她走来,有些惊慌地呆在原地。
狱警告诉她,刘远征今天早上从监狱逃跑了,我们找你了解点情况。
素芬半天没回话,带路的村长催促了几遍,她才答非所问地开口:“我和他离婚了。”
狱警不太在意地点点头,又想把话绕回刘远征。
素芬低着头,突然把袖子捋了上去,直到露出上臂,伸到狱警面前。
手和小臂都很正常,就是一双普通人的手。但一过肘关节,往上全是密密麻麻的伤痕。有烟头的烫痕,有被刀划开的整齐伤疤,还有些扭曲像蜈蚣一样的疤痕。
她的上臂就像一件不成功的根雕。
“这就是他上次回来留给我的,全身都是。”素芬声音好像收到了头顶阳光的热量,渐渐恢复了正常的语调,“所以我和他离婚了。”
一个半月前,刘远征改变越狱计划的那一天,就是素芬提出离婚的日子。
素芬要离婚的事情,早在几个月前的信里给他说过。刘远征看到那封信后,两天几乎没有吃饭。后来素芬强行起诉,法院受理,直接派了工作人员陪她来办手续。
带刘远征去接见的干部有点尴尬,他以为是去接见家人的,没想到是办理离婚。
一般坐牢的人,遇到妻子想离婚都会很激动。作为管教干部,最忌讳罪犯情绪波动过大,万一想不开,闹个自伤自残甚至自杀脱逃的事儿出来,那可就是监管事故了。
他试图劝一下刘远征的妻子,男人在服刑,能不能考虑一下孩子和双方家庭,缓一缓再决定是否离婚。
“报告干部,我们没得娃儿!”刘远征主动开口,语气很平静,“谢谢干部关心,不用劝她,我同意离婚,我签字。”
刘远征看着眼前的女人,这七八年好像没什么改变,还是年轻漂亮丰满动人。素芬还是那个素芬,毕竟外面的生活和在劳改队坐牢区别还是很大的。
“那我就真的签了哟,素芬。”
刘远征盯着素芬说这话的时候,在场的人都能看到她非常紧张和害怕,双手在桌子边沿很用力地撑住自己身体,力量大到让指甲在桌子上留下抓痕。
可是她对面的男人什么也没做,只是一笔一划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刘远征”三个大字终于落下,素芬似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放开桌边。平静了一会,她低声嘱咐刘远征说,自己最后给他上了三百块钱在账里。
刘远征带着点笑容说:“那就谢谢你了。等我满刑回来,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素芬几乎一下就从椅子上弹起来,拼命摆着手说不要,夺门而逃。
两天过去了,按照计划,刘远征只要在原地再等几天,警察就会撤岗,他就可以去找素芬了。
但他忘记了一件事,自己等下去的前提是必须要有食物,而他已经没食物了。他只吃了两个馒头,现在正饿得胃痉挛。
他摸到井口看看,天早就黑了。
他想到山下一户相对落单的人家,和家属区隔得比较远,他上次服刑的时候认识那家人,家里只有老两口,实在不行要抢,他也抢得过。
门一打开,老头很惊讶,刘远征也吓了一跳——老头手里拿了一根棍子!
他头皮一紧,下意识地就要把胳膊往前挡。老头看了他一眼,咳嗽着拄着棍子往边上让了让——那是他的拐棍。
警察白天四处找人,老头当然也知道刘远征现在是个在逃犯。但他一把年纪了,不敢跟刘远征硬碰硬,只能旁敲侧击地问刘远征为什么越狱、劝他回去自首。
刘远征说好,但现在太饿了,想先吃点东西再去投案。
老头由着刘远征把柜子里的酥肉拿了煮汤,合着一点剩饭,吃得实在动弹不得了才放下筷子。
老头发了一支手工卷的叶子烟给他说,我现在陪你一起去投案最好。
刘远征靠在椅子上,又说自己怕回去关禁闭没饭吃,求老头给他收拾点酥肉和叶子烟,以后让舅舅还给他,说完又拿了一件衣服。
老头一一照做,给他装了好大一个袋子,拄着拐棍陪他一块去自首。
刚一出门,刘远征抱着袋子就跑,老头在后面跺脚大骂,等周围人听到跑出来时,人已经消失在黑暗中。
得知刘远征再次在监狱警戒线之内出现,领导气得拍桌子,说跑出去了也就算了,一直躲在我们眼皮底下却捉不到,岂不是把我们当猴耍。
其实,自从我们知道刘远征去找舅舅,就推断出他并没有跑远。可是人到底在哪里,也不好找。
监狱其实就是一个煤矿,警戒线内是整整一座山,能藏人的地方太多了。
监狱几乎全员出动,把所有闲置的房屋翻了个遍,绝大多数估计能藏身的废弃井洞也检查过,重点的几个还让救护队人员带了呼吸器进去搜索。
追捕小组甚至把附近的泥煤池全放到见底。泥煤池像水一样,人可以潜在里面,之前就有个罪犯躲泥煤池里,直到憋不住上来喘气才被我们抓住。
我参加过很多次追捕,但把在外的人员撤回来,就在监狱警戒线之内追捕的事,还是第一次遇到。
监狱内能用来藏身之处,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可刘远征还是不见踪影。
刘远征在井下又度过了三天,前后一共五天了。
每天,他摸索到井口,四周看看没人,然后退到视觉更隐蔽又不至于引燃瓦斯的地方,划一根火柴,点上老头那儿抢的烟。
等过足了烟瘾,再借着烟头闪烁的微光,回到巷道到深处睡觉的地方,就这样来来回回。
他甘愿忍受这些,是因为一直觉得,素芬欠他一条命。
那年两人进城后,每天上工下工,到月底一算,连块肉都吃不起。街上的馆子飘着回锅肉的香味,都和他没关系,他好像根本没离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照样辛苦,照样窘迫。
和他一块喝酒的也还是那几个老乡,但人家却个个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抽的是红塔山,喝酒时多请他一顿也不在话下。
刘远征旁敲侧击地问他们在哪发财,老乡推辞两三句,神神秘秘地告诉他,他们在工地“拿货”去卖。
说是“拿货”,其实是偷。工地的钢筋、建材,家伙大,看守的人也就粗心,几个老乡分工,一批放哨、一批搬货,一趟能挣他们两口子一个月的钱。
刘远征老实了半辈子,这种事想也不敢想。老乡们也不逼他,照样在他边上抽红塔山,酒局散了,几个人勾肩搭背往工地走,刘远征一个人回家。
这样的日子没有坚持多久。
小两口结婚两年也没孩子,趁着医院,刘远征把俩人都上上下下做了个检查。结果医生说他们都没问题,顺口嘱咐他,“想怀孕要注意增加营养和少熬夜”。
“增加营养”,这四个字一下戳中了刘远征的痛点。要不是挣不到钱,他会让媳妇饿肚子吗?他老刘家到现在都没后,全是这个穷字害的。
再跟老乡们喝酒时,刘远征就留了个心眼,有意无意地提起他们“拿货”的生意。
老乡在旁边煽风点火:“素芬这么安逸的婆娘,你娃不多挣票子好好养起,说不定过几天跟别个跑河南跑福建了,那你娃不是一样瓜兮了。”
刘远征顺水推舟:“要得!我听哥老倌的,干!”
此后,刘远征就算入伙了。不仅是他,素芬也一起去了。在男人们拿货的时候,女人就在一旁踩点放风。
第一次偷钢筋的时候,他们被守工地的人发现,撵出去好远。刘远征差点跑不动了,放风的同伙装喝醉酒,骑着自行车绊倒了追兵,他才脱身。
和老乡们汇合后,刘远征才发现自己刚才紧张得尿了裤子。
团伙里的老大轻描淡写地从赃款里拿了块钱给他,让他拿这钱去买条好裤子。
这一趟下来,刘远征拢共得了块钱,两口子一个月都挣不来的块。
刘远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平日上工,有闲就去“拿货”。渐渐也能抽上红塔山,也能大鱼大肉了。
在七个月左右时间里,刘远征和老婆赚了小一万块。
素芬是当时典型的农村姑娘,也不知道对错,但对刘远征死心塌地。他们越来越像个“城里人”,就差一个孩子,就算在城里安下了。
但他们没等到那个孩子。
在一次拿货的过程中,他们被工人逮了个正着,扭送到警察局。老大判了十年,刘远征判了七年。
刘远征进了监狱,再一次看到素芬,隔着探视窗,她又是哭、又是不停地问他缺不缺钱。两人眼神一对,刘远征在她眼中看到了恐惧。
他们被抓住的那一次,素芬就在不远处望风。她是同伙,她也该坐牢的,是刘远征袒护了她。
酥肉真好吃,可惜是最后一块了。一片漆黑中,刘远征慢慢地咀嚼着一小块酥肉。
他知道两次露面后,邻居大娘和那个老头一定会去报告,原先指望狱警们撤掉卡点已经不太可能。他必须弄到更多吃的,熬得再久一点。
他挑了一个雨夜,再次小心翼翼地摸索到舅舅房子附近。
兜兜转转一圈,他又回到了舅舅家。
一个巡逻的人都没看见,刘远征悬了一个多小时的心终于放下来。
上次惊醒邻居的教训让刘远征不敢再贸然敲门,他慢慢地摸到窗户根,想听听屋里有没有人。窗户靠着舅舅的床,如果有人,他轻轻敲下窗户就能把舅舅叫醒,免得惊动旁人。
下雨的声音和屋檐水流下来的声音严重干扰了刘远征,但他很耐心地听了几分钟,终于听到床上有人翻身的动静。
应该是舅舅回来了,刘远征暗自庆幸今天运气不错。
抬起手的一瞬间,他听到屋内有很低的说话声——舅舅一个人住,和谁说话?
不对,老子差点上当!
刘远征死死攥住准备敲窗的右手,在夜雨的掩护下,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靠着墙根离开。
“哐当!”天太黑了,他完全没反应过来时,木板已经在他脚下砸出响亮的声音。
屋里的人冲出来,刘远征拼了命地跑,手电从四面八方射过来,他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埋伏。
前面的每一个路口肯定都有人守着,电光火石之间,刘远征脚下一转,往一个死胡同跑去。
果然没人!
刘远征蹿上巷子尽头的墙,毫不犹豫地从悬崖跳下去。虽然有七、八米的高度,但刘远征知道悬崖下面是泥煤池,像沼泽一样非常松软,这个高度跳下去,只要着地的时候注意姿势,就不会受伤——
脚踝传来的骨裂声告诉他,他错了。泥煤刚刚被搜他的狱警抽了个干净,他狠狠砸在地上。但一瞬间他感觉不到痛,囫囵爬起来拖着伤腿继续跑。
翻上泥煤池,又从四五米高的河堤跳下去。他不敢再用脚缓冲,背部触地时,他感觉到一块突出的鹅卵石正好撞在脊柱上。
还是没有感到疼痛。刘远征近乎麻木地爬起来,拼命向河对岸跑。
那条平时不过两三米宽、及膝深的河,因为这几天的雨竟然涨到了十来米宽,水也差不多淹到胸口。刘远征疯狂地冲过河,爬上对岸七八米高的河堤,穿过公路、钻进山林。
他已经感觉不到脚、感觉不到脊背,只知道躲进密林里才有可能逃掉、才有可能出去杀了素芬。
刘远征第一次刑满出狱回家,心里忐忑不安。
在监狱蹲了五年,他常常听狱友们说,女人靠不住,不会再外面等自己的男人。事实也好像确实如此,素芬来看他的频率越来越低,最后干脆不来了。
刘远征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怀疑,素芬是不是有人了,会不会已经跑了。
他刑满回家时,素芬并没有跟人跑。但他并不高兴,因为素芬穿得明显比当地女人时尚。他坐牢前,素芬可从来没穿过这么洋盘的衣服。
他想,这八成是有男人了。
他又看了一眼房子,还是和进去的时候一样。要知道当年的赃款警察并没有完全没收,完全可以再盖一间新房子,但素芬没有这么做。
他觉得,素芬把钱都花在了自己打扮上面,她好像忘了自己本该老老实实地穿着囚服,和他一样。
她始终没有怀孕这件事证明,素芬不想给他老刘家传宗接代,早晚会跑掉。
当天晚上睡觉,素芬脱下外衣时,刘远征看到不再是以前的小背心,素芬居然是穿了城里人才穿的胸罩,几十块钱一对的胸罩!他再也忍不住了。他伸出手,狠狠打向了素芬。
从此之后,刘远征便开始虐待素芬,用各种能想到的办法折磨她。
这些痛比起他坐牢的苦,算什么?他只是在把素芬该受的惩罚还给她。
刘远征死死拽住素芬的同时,也打算重新找回自己的“事业”。
他从监狱离开的时候就计划,找到监狱里认识的大哥,一起赚大钱。
可是大哥没找到,又碰到以前一起偷东西的老乡。刘远征想都没多想,立刻回归到以前的生活里。
他不怕被抓,在监狱的后半段时间,他是个小组长,每天带犯人出去修路,也不用干活,活得很舒服的。
他甚至说,自己有时会想念监狱的生活。
三个月后,刘远征“如愿以偿”,又被抓了起来。
刘远征拖着脚,爬到一个大石头下面,最后拉了点灌木挡住洞口。他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最近的时候不超过十米,人吵成一团,甚至有手电光扫过来。
但人群也只能追踪到公路上,这面的山太多了,全是山林。他觉得,这样的雨天晚上,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人来仔细搜山。
刘远征得意地笑起来,脊柱的疼痛又瞬间让他闭嘴。在石头和地面之间的夹缝里,他躺了整整一天。
如他所料,我们几百人在把这片山林来回翻了个遍。甚至在兄弟单位借了警犬来帮忙,可能是断断续续地雨水冲刷干净了痕迹和气味,警犬也没有找到更多线索。
雨一直在下,山上甚至飘起了雨夹雪,搜查的武警和民兵都累得筋疲力尽。
我们不能一直这么耗下去,最多再过两天,外面的卡点也会撤除。而刘远征,就会成为历年在逃未捕回名单上的新名字。
夜幕降临,雨也停了,刘远征艰难地爬出来,找了两根树枝,撕下几缕衣服,做了个简易夹板,固定好已经完全失去知觉的左脚,又找了一根长一点树枝当拐杖,一瘸一拐地向有灯光的地方摸过去。
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第一次劳改的时候他主要在这段修公路,这里有一户他熟悉的人家,有一位留着长辫子的姑娘。
他曾向她吹嘘,自己是贪污犯,在外面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单纯的村姑很容易就对他产生了崇拜。那天找了个来她家借工具的机会,就在这儿,刘远征得到了她。
他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对不对得起素芬。
柴房挨着灶屋,刘远征听到堂屋里有人在打麻将。他竭尽全力控制自己的身体移动,在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的情况下,开始寻找食物。
有一些剩饭菜,更幸运的是灶里居然还有火。刘远征凑过去,吃了一点东西后才注意到自己坐的凳子上垫着不少旧衣服,其中居然有一件旧棉袄。靠着灶边,还烤着一双洗过的胶鞋。
刘远征脱下全身湿透的衣物,换上干燥的旧衣物和鞋子,温暖舒适的感觉甚至暂时让他忘记了身体的疼痛。
突然,一只碗摔在地上,声音非常清脆响亮。是一只可恶的耗子干的。但屋里的人被惊动了,往厨房走来。
刘远征抓了一大把灶灰,等那人一进灶屋,直接撒在他脸上,起身就跑。这家人后来形容,“像鬼一样,一下就找不到了。”
黑暗中他很快冲上山顶,把追他的人远远甩在身后。当他正在疑惑为什么自己如此厉害的时候,脚下却空了。
不是受伤的虚脱,而是直接掉下了悬崖。
刘远征第二次入狱后,看到自己被判十二年,又要下井劳动,立马就后悔了。这个刑期太长,他等不了,一进来就打算逃走。
他计划直接去广东闯荡,但是一封信让事情出现了意外。那是他进来之后刚刚一个多月,素芬寄信告诉他,自己想离婚。
监狱的信件都是要被拆开的,狱警得先读一读有没有不符合规定的。当看到这封离婚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得做刘远征思想工作了。
男人进了监狱,女人要提离婚太正常了。我们劝刘远征,看开一点,没有孩子就离了吧。
刘远征在狱警面前表现得很正常,口头上说自己没事。但回到监狱,他独自生闷气,情绪低落,连续两天没有吃饭。
当素芬带着离婚协议来到监狱的时候,刘远征很快签下了字。狱警再次找他谈话,他还是表现得很正常,狱警也就没放在心上。
其实那段时间,刘远征已经起了杀心。连续好几天,狱警在的时候他就装成正常人,一旦狱警不在了,他就郁郁寡欢的样子,一个人在角落发呆,话变少了,饭也吃不下。
他开始有意识留头发,为以后出逃做准备。
监狱十天左右给囚犯剪一次头,发型只有一种,光头。刘远征每次计算到理发时间,故意让自己拖延加班。狱警有时也工作疏忽,就把他给忘了。
两次没剪头,刘远征看起来就和外面的普通的平头一样了。
接下来他又在运煤的司机那里骗了两件衣服,藏在煤仓附近。
万事俱备,他只等着去杀素芬。
他还在七年前的原地,凭什么素芬就可以离开?她做梦。
刘远征醒来时,居然看见了太阳。
从悬崖上摔下去到现在,他昏迷了五十多小时。刘远征试着动一下身体,除了极度虚弱无力,他感觉自己还能勉强站起来。站起来的同时,全身每个关节都传来的疼痛直接让他惨叫。
在接近原始状态的山谷里,他的哀嚎甚至没有回声。
他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只能感觉到浑身被碾碎了一样的剧痛。勉强站起来,只挪动了一两步就开始剧烈地咳嗽,拿手一捂,手上全是咳出来的血。
他明白这次摔下来的冲击,已经严重地伤到了内脏。
刘远征试图叫救命,可是他声嘶力竭的叫声听起来并不比自己的呼吸声大多少。
难道要死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山崖下面?
可是素芬还在家里逍遥呢。
刘远征手脚并用地爬上了悬崖,眼前一阵又一阵地发黑,他拄着一根树枝,一步一挪。早知道当时就该直接往外跑,在监区转了这么久,最后反而更加狼狈。
他仅剩的一线希望,就是指望自己已经越过了封锁线,只要走出树林,早晚可以爬回家杀掉素芬。
天几乎全黑了,影影绰绰看见前面有一间亮着灯的屋子。刘远征根本没再想里面有没有人,也没想会不会被抓,他直接走了过去,奔进灶屋里寻找吃的。
刚好洗刷过的锅里连水也没有,只有灶头屯着一大瓶清油。刘远征毫不犹豫拿起来,咕嘟咕嘟大口喝下去。从来没想到生菜籽油原来这么香。
旁边的柜子里还有两把挂面,刘远征抓起面条猛咬一口,干硬的面条戳破了他的嘴唇和口腔。顾不得这么多了,他胡乱咀嚼几下,和着清油吞下去。
突然刘远征听到有人在说话,两三个人正向屋子走来。他把挂面揣进怀里,再一次开始逃窜。有粮食、可以喝雨水,他还能跑。
这一次,他最后坚持了一夜。
天放亮时,刘远征从树丛里探出头来确认自己现在的位置。当他看到山脚的检查站时,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架——跑了这么久,还在警戒线里!
刘远征绝望了。从坡上直接滚下来,一直滚到路边停下,不再挣扎,像一具尸体一样躺在那里。
他最后是被几个老乡发现的,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着他过来。
他一句话都没说,看到监狱的人,脸上没有怨恨或恐惧,反而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
我们也确医院,上了那时候最昂贵的监护仪,尽全力想救他。
在刘远征家里蹲守的追捕小组也撤了回来,听他们说,素芬听说刘远征摔伤,一点难过的样子都没有,面无表情地说了句“摔死了才好”。
几天后,刘远征抢救无效,医院。家人接走了他的骨灰,而他的名字和档案袋一起,永远留在了监狱的柜子里。
我一直记得他最后躺在病床上,蜷缩在被子里,回忆他和素芬的恩怨。他已经很虚弱,说几分钟就不行了,整个人像一抹幽魂。
但是,当他说到年轻时带着素芬离开农村时,突然有了精气神,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当时,刘远征一定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闯出一番天地,但我觉得他哪里也没有去成。
他计划躲在山上就能越狱成功,但是把自己熬死了;他要去社会上闯荡,但两次经历都是在盗窃;他不肯放素芬走,要她永远陪自己,但最后还是离婚了。
这么多年,他一直被困在原地。
唐有耳在监狱干了二十多年,越狱的事情没少听说,但是跑掉后一直在监区打转的只有这一个。
“打转”这个词让我想起自然界有个很著名的现象,叫做“死亡漩涡”,是说行军蚁有时候会围成一圈,不停地打转,直到死亡。
行军蚁没有视力,只知道沿着之前留下的气味不停地奔跑,一旦之前气味错了,他们就会自己累死自己。
刘远征的人生也很像踏入了一个死亡漩涡,他不停陷入到原有生活的轨迹里,却自以为正在向前进。
他可能没想明白,如果前进的目标错了,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
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困住他的高墙不在外面,而是在他心里。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马修卡西尼
插图:娃娃鱼
这个故事选自「天才捕手计划」的系列「流放之地」,他们还有很多精彩的监狱故事。
一个19岁的少年犯强奸了心爱的女孩,他说只有那样做,才能救下她的性命。
少年小武被别人欺负,第一次鼓足勇气反抗就失手杀了人。他被判死刑,被关入一间“死囚房”。三个大哥听到他的故事,得知他可能未满十八岁,准备帮他翻案。
这是他们的